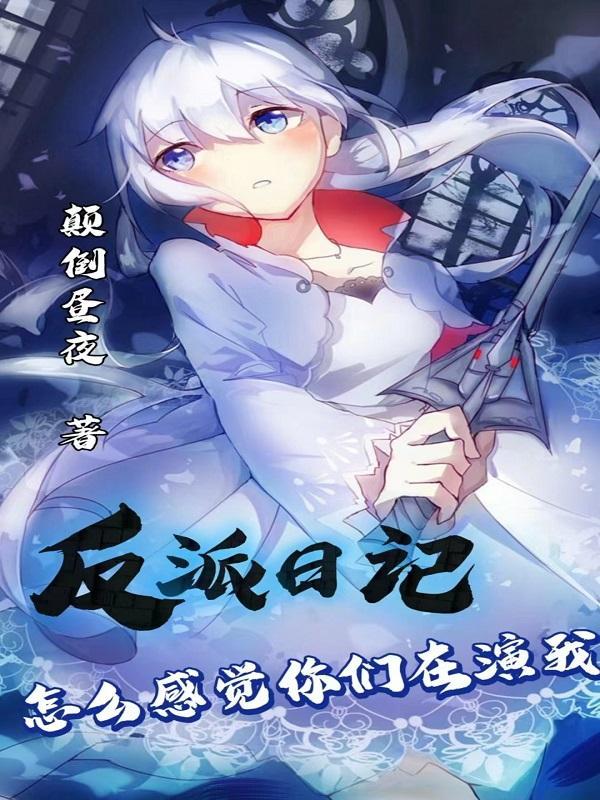第七中文>焚化炉口供 > 珊瑚礁之夜(第6页)
珊瑚礁之夜(第6页)
小林冷哼一声:“如果他不存在财务危机,以他的名头,还有他办不到的?难道他要长生不老、拉着家人和所有孩子一起长生不老?”
“不不,太夸张啦。”
“也是,说不通了。有什么事情是他非得拿疗养院做噱头,凭一己之力却做不成的?”
“那就很少很少啦。”幸惠摸了摸下唇,每次嘴唇与皮肤的摩擦都让她萌生与人接吻冲动,“……也许是改变人的本质?……”
全身湿淋淋的,她的喉咙却干燥得难受。于是她不再说话了。
小林自言自语地规划下山之后的调查思路:他坚信真相藏在疗养院创立始末和八神夫妇的身世背景里,他要弄清浦口究竟为何偷窃又为何疯癫逃离直至坠崖,他得想尽办法把北海弄出去体检,他再不济就逐一彻查院中孩童与雇工的来历,他可以学着前辈——影视作品中的同行们——那样请来民俗学家帮手;还有八神爱,或许她身在西洋的亲生父母也牵扯其中。无论如何,他不能放弃行动派的展望……呃,他呜咽了一声。他的胃部似乎出现了轻微不适。
幸惠不忍心告诉他:等到节目录制完成,这桩案子就结束了。
她最终没把残忍的话如珍珠一般吐出来。
因为她的头脑陷入不知缘由的眩晕了。
幸惠走到一半,被诡谲的亢奋缠上了。她忽然诞生了转身跑开、独创一个人间的勇猛。
脚底下有啧啧的水洼声。最初是脚踝骨有些痒,然后水滴从腿骨往上爬,两块膝关节变得沉甸甸的,再经过胯骨,脊骨,变成吸饱了水的棉花,一心想着坠落回泥土间。人的灵魂寓居在脊髓里,针管抽出一剂髓液来,显微镜下大概还有花团锦簇的狂喜的细胞状魂魄在跳舞呢。骨骼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寂寞的,内里空虚不堪的。中空的骨腔迸出白光来。
幸惠张口呼吸,公立医院的棉球就堵满了她的气管。乖,张开嘴。护士说。然后是双腿。无影灯的光芒落在她脸颊上、鼻尖上、眉毛上、牙齿——她自恃细白整齐的牙齿上,酥酥麻麻的,又无可辩驳地执行着正义。她的眼前飘过一些幻影,从肉胎中挣扎起来的幻影,模拟着传说里爱人的许诺的幻影。她跌下床,咬破了舌头,“啊——”地张大了嘴对镜自照,口腔的软肉上钉着一枚新月状的牙齿咬下的血痕。当时她哭了起来:除了这个,全身上下再没有她能掌控的了。她引以自傲的意志原来是像蛞蝓一样的脏东西,浇一勺粘稠的盐水就把她杀灭了,而她最初淋了那水时还在大开眼界地洋洋自得。你才十七岁,那个男人应该承担责任。护士严苛地折断她。她盯着她傻笑,笑到腰肢以下全在痉挛。
她想:如果她不能改掉反复抓住热气球贪图攀升至天国的热情,那么至少,她下一次要换乘大一点的、漂亮一点的气球。再做梦做得美满一点,有朝一日,她的躯壳能否同她的意志完全融为一体呢?
她正是在此时,第一次与它相遇了。
东,西,南,北。一般而言,这是四根走出稽山的救命稻草。指南针不在幸惠手上,但她的右腿突然疲惫地弯曲,转向,左腿跟上,拖拽着她往一棵树皮疤痕像是孔雀花纹的梧桐树走去。从下往上,海涛拍岸,黑色的潮汐盖过了淅淅沥沥残雨的哀泣,它对她吐了吐圆环状的舌头,那样子很美丽,一切都清晰、简朴、明确。
她马上明白了尸体的断颈为何长出圆环。从古至今——固然K城是全无一点古韵的城市,历史的“可考”约等于“可疑”——圆都是最富装饰性的图案。项链,耳环,手镯,戒指,脚链。环佩可以相鸣叫。最好的是完璧,不过今时太笨重了,适宜纳入博物馆。哎呀,她想起了她从古玩市场淘来的一副最满意的珍珠耳坠。如果她笑纳贡品,她也不要千金重礼,只得些亲手挑选的一流玩艺,每日不带重样,乐趣也就够了。
它凑上前,舔了舔她的眼球。她的左眼立即从根部变得热乎乎的。然后是食道的存在,温暖、干燥、酥脆,咀嚼饼干的口感一路向下蔓延,连同胃囊也独立出来了。她笑了起来,咬了它一口,咬断一截树枝状的残骸。舌苔火辣辣的,她眼泪流下来。她一边吃它,一边放任它帮自己颠倒顺序,重组肉身。它按了按她的骨盆。那么,一切重新来过?它说好的。
突然幸惠左手被烦人地拽住。有人剧烈摇晃她的双肩,她就故意呕吐在了那人脸上。
其实她并没有呕出什么来。眼前只剩一个惊恐万状的小林:
“你流血了!眼睛还看得见吗?”
幸惠这才感觉左眼糊了一层粥水。她气恼地甩了甩脑袋,说:不知道怎么回事!不肯死心,继续朝那方向迈步。
这回她整个人被小林拖住了。她叫道:“拜托!我有急事!我要去那边!”见小林僵持,她双手搭在他手背上,又挤出讨价还价的温柔话:“就等我一下下?或者你先去啦。”
她努力甩了两下,没能甩开刑警。她真的生气了,跺脚吵嚷起来,指着他鼻子威胁他松手。
他死死拽着,咬牙切齿半晌,终于软下性子,央求她:
“幸惠,你不能走。我们是搭档。”
他断断续续说:……如果我们没有一起下山……还算什么搭档?
天哪,他快要哭了。
幸惠噗嗤一笑,雨水又大起来。幸惠也不是十七岁了。
幸惠冲小林眨了眨眼睛,说声多谢,心虚地回头一望:空中一无所有,只剩黑魆魆的树影。她什么都没吃下,腹中仍然很饿,是缺乏了夜宵的饥饿。小臂粗的树枝咔嚓坠地,如果她再往前两步,砸到头上,或许会得脑震荡。
她顿时有种不祥预感,猛地一拍小林,推他往左拐。小林莫名其妙:“你不会又要……”等他被她拽上了斜坡,爬到一块平地上,他顾不得幸惠了,再度大惊失色。
阴差阳错,他们重返了抛尸地点,土坑中原本堆积如山丘的落叶被砍去一半,整个深坑的表面似乎也萎缩了。然而:
“谁躺在那里?”
坑中仰面躺倒一具断气不久的尸体,正是北海玲乃。
幸惠扑去跪在坑边,探手去摸她腹腔,珊瑚枝却不见了,只摸到一个坚硬的圆球状的东西。
她什么都忘却了,双手抠住那东西的凹槽将其拎出来,高高捧过头顶,借着闪电眯眼一看。异物无缺如白璧。
一颗森白颅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