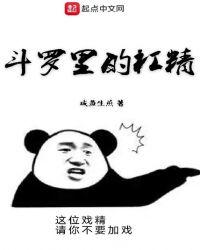第七中文>夺娇 > 第268章 劝说(第1页)
第268章 劝说(第1页)
京城的雪洋洋洒洒地下了七八日,终于在大年三十的那天放了晴。
久违的阳光照在院子里的积雪上,显得格外的耀眼。
因朝廷在大年二十七那日就封了印,大臣们不用再上朝,姜闵中自然也不用再进宫给太子讲经。得了闲的他独自在书房里围着火炉品茗观书,倒也没拘着青松他们这几个小厮,而是任由他们在院子里玩闹。
孟德全和往年一样,早早地就派人送了一大车年货过来,其中就有一大箱子炮竹和烟花。
因姜宁对这些都不太感兴趣,姜闵中便将这些烟花炮竹都赏给了青松他们。
几个小子就在院子里零星地点起了炮竹,噼啪的爆竹声就让年味更浓了。
一脸病容的裴太太和衣靠坐在临窗大炕上,膝上搭着一条半新的薄棉被,听着屋外的炮竹声,却在愣神。
她和裴晅住进来已经有些日子了,除了第一日听到姜老爷在院子里嚷了那一嗓子外,她就再也没听到过他的声音,更别提同姜老爷打照面的事了。
而那日做主将她接来的姜宁后来也不曾露面,反倒是住在隔壁的石婆子来得有些勤快,三不五时地陪她说说话,聊一些有一搭没一搭的事。
还有先前对她冷脸相待的沈太太,嘴里说着要让她自生自灭,却还是悉心照料着她的饮食,在用食疗的法子帮她弥补着身体的亏空。
一想到这,裴太太的心里就泛起了苦,越发不知道要如何面对住在这个院子里的人了。
“娘,该喝药了。”裴晅端着一碗黑浓的汤药进得屋来,服用了许大夫开的两剂小柴胡汤后,他蒙在被子里发了一场汗,烧就退了下去。
感觉恢复了一些力气后,裴晅便像以前一样服侍起母亲的日常起居。
裴太太没有接药碗,而是抬眼打量了儿子一眼,这才留意到裴晅这两日穿的竟是件七八成新的灰布棉袄,因为有些宽大,他将袖口向上挽了两圈,露出了一双红肿皴裂的手。
裴太太看得眼神一黯,落在裴晅的眼里,就让他莫名紧张了起来。
他拘促地拽着衣襟:“沈伯母瞧着我之前的那件棉衣有些短小,执意要我穿沈伯伯的这件旧棉衣……”
这拘谨的模样和颤抖的声音,仿佛一根尖刺扎进了裴太太的心里,也让她明白了之前姜宁的指责。
想起一年前的裴晅还是活泼开朗又自信的样子,裴太太抬手就扇了自己一耳光。
“娘!”裴晅惊愕地放下药碗,伸手抱住了裴太太。
“我这一年到底都做了什么呀!”裴太太就开始捶足顿胸地哭了起来。
一开始她只是在小声呜咽,随后哭声渐渐变大,偶尔夹杂着一两声哀嚎,到最后竟是嚎啕大哭。
裴晅再沉稳,可到底才十岁上下的年纪,没经历过这些事的他只能手足无措地抱住了母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