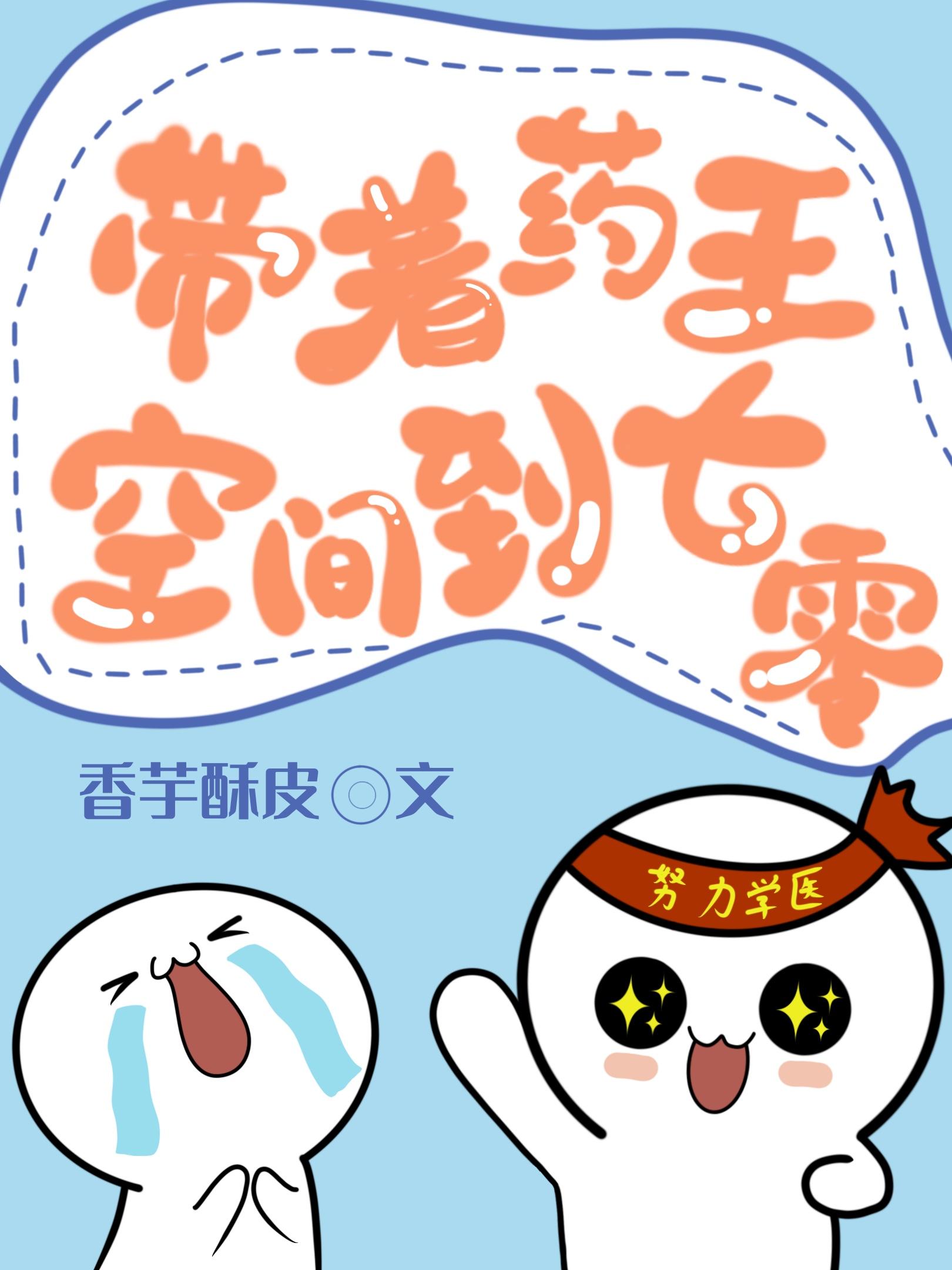第七中文>美人掌欢[重生] > 第183章(第2页)
第183章(第2页)
岑迦南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美景,一只黑眸黑如点漆,一只紫眸艳如骄阳,他似是被抽了魂,受了蛊惑地朝谈宝璐走近。
他并不觉得自己的举动有什么不对,这是他的女人,以后他们还会做更亲密的事,现在这只是一点点饲狼用的开胃小菜。
谈宝璐却被逼得连连后退,她光着的脚到处踩,脚掌踩着了衣摆,几乎跌了一个趔趄。
她腾出手,要去扶身后的浴桶,岑迦南恰到好处站到了她的面前,一把托上了她的臂膀,将她拖抱了起来,他借机把她往自己怀按,沉声问:“为何不肯回去?”
感觉岑迦南的手掌肉贴肉地扶在她的后腰上,谈宝璐登时身体发起抖来,“殿下,快放开我……”
以往岑迦南再怎么抱她、碰她,就算滚到床上去了,两人之间也隔了几层衣物。她还是体面的,不像现在这样,衣不蔽体,难堪到了极点。而且岑迦南亲口对她说过,绝不会勉强她做她不想做的事。
她又想到母亲叮嘱她男人的狭隘小气,便觉得岑迦南今晚是故意为之,将她当作玩物看待。
她在岑迦南怀里像小鱼似的挣来挣去,又推又搡,说:“松手,殿下松手!”
岑迦南也不是泥做成的人,他的脾气又狂又自大,想做成的事,纵千军万马不可敌,在谈宝璐面前不过是压了三分本性。
他连日在外带兵打仗,手下人又被赫东延折了不少,案几上的公务堆积得有一人多高。公务糟心也就算了,下头人还办事不利,今日几名幕僚来禀事,说的话牛头不对马嘴,将他惹出了一肚子火。好不容易入了夜,他一到家就听随从说谈姑娘不肯回他这儿,这下是真一脚踩到了他的禁区。
他向来喜欢谈宝璐乖巧温顺的样子,嘴又甜,跟他浓情蜜意时句句称他心意,如今这么一朵“解语花”,在他怀里像只炸了毛的兔子,恨不得要跳起来咬他一口,岑迦南的火气终于忍无可忍。
他声调沉了几分,紧紧钳着她的手腕,道:“不许躲着我。”
谈宝璐手中的纱衣要掉到了地上,那是她最后的一丝遮挡,她更加用力地抓着那层布,即便只是徒劳,“我要洗澡了,岑迦南我要你出去!”
谈宝璐反抗得越厉害,岑迦南越觉得她也在厌恶自己、排斥自己,就跟他身边的所有人一样。
所有人都想尽办法逃离他的身边,想尽办法不与他产生联系,即便是血浓于水,也要割断。
他的头疼起来了,一抽一抽得痛,痛疼让他的脸色阴沉到了极点,那只紫色的眼睛烧得几乎要往外滴血,理智全无。
他紧抱着谈宝璐,竟将她抱进了浴桶里,“想洗澡,我给你洗就是了。”
谈宝璐手中的纱衣在拉扯中落到了地上。
温热的水流将她严丝合缝的包裹起来,反复提醒着她,她如今在岑迦南面前同赤身没有什么区别。白色的雾气升起,朦胧了她的眼睛,让她分不清那是水光还是泪水。
()
|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