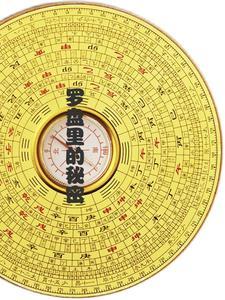第七中文>(火影忍者同人)[火影乙女]我的百分百被一见钟情Buff原来是对宇智波特攻吗 > 第44章(第2页)
第44章(第2页)
倘若不是因陀罗态度忽然转变,这个计划原本不会有任何纰漏。
如果能调查出对方的来历,似乎就能搞清楚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,以及制止他们的后续行为了。
包在纸巾里的是几根深棕色的长发发丝,在无光的暗处,近乎黑色。另一件则是白色的高领风衣,在雪白的领口附近环绕着黑色勾玉刺绣。
这是我当时借机留下的证物。
白风衣的衣袖上有一道大约十来公分的划痕,破碎的布料附近晕染着早已干涸的鲜血。
我的手指情不自禁地抽搐了一下。
这是我弄伤因陀罗时留下的。
沾血的手掌早已洗净,被小樱仔细地消毒并包扎。但指尖依然残留着那种陷入湿热泥泞的肉脂里,被涌出来的大股温热鲜血所包裹的触感。当我试着撕裂他时,食指与无名指深深陷入狭缝间,血管、筋络与肌腱宛如藤蔓般纠缠着我,引着我往下与他融合,一直触摸到坚硬温热的臂骨。
灵魂在战栗。
现在想来,那时我掌心伤口渗出的鲜血,是否与他伤口里血液融合在了一起,渗入他的骨血中。
因此我愈是拉扯撕裂他,给他带来强烈的痛苦,愈是令他兴奋颤抖。
像是陷入温热的黄油。像是撬开牡蛎的硬壳。
柔软、湿润、滚烫。
疼痛将孕育出美丽饱满的珍珠。
令人上瘾。
与我不在同一个世界的,令人毛骨悚然的疯子。
这间临时征用的医务室对这么多人来说有些太狭窄了。纲手老师和小樱留下来看顾病人。我和鸣人暂且出去交流。
木叶大学的黄昏是一天中最悠闲的时光,赭石色的夕阳柔柔照耀,一天的课程大半结束,学生们三三两两并肩散步,或是说笑打闹,或是奔赴餐厅,或是在体育馆锻炼。
草丛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,我蹲下身,看见绿叶被一个漆黑的、湿漉漉的小鼻子拨开。那黑鼻子优雅地嗅了嗅我的手指,接着黑色的深渊豁然横向裂开,探出来一条粉色的猫舌头舔了舔,接着,草丛里钻出来同样黑漆漆的一只炸毛小黑猫。
“呀,是你呀。”我说。
话音刚落,就像是捅了猫窝,原本还空无一物的草丛里猛地探出来四五双高高竖起的、黑色的毛茸茸猫耳朵。猫咪们喵喵呜呜地钻出来,眼巴巴围着我。
因着黄昏时光线暗淡,细针似的猫瞳扩展成圆溜溜的一片。转瞬间,我就这样被一大群眼睛圆溜溜的黑漆漆的东西包围了。